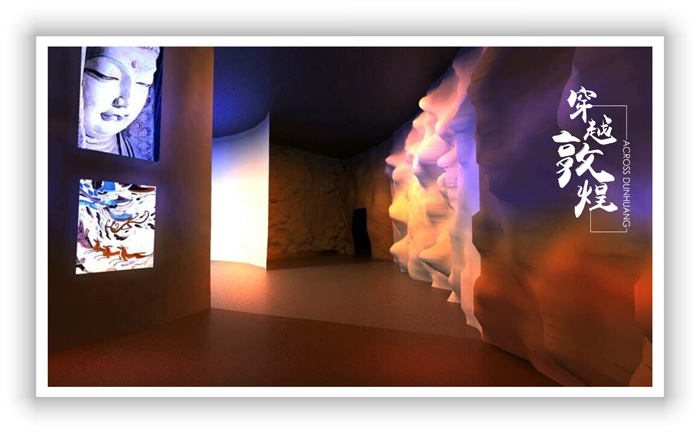中國畫壇怎么就成了江湖?
市場說了算?
1992年,一位畫商走進一位藝術家的工作室,驚奇地發現眼前堆積了那么多的精彩之作,心中竊喜,卻故意面無表情。藝術家則誠惶誠恐盯著畫商的一舉一動,生怕這位財神擦肩而過。最后,在藝術家千恩萬謝下,畫商以難以置信的低價把其作品全部搬走。請讀者相信,這不是虛構,這位藝術家現在已是公認的大腕,作品早就成了市場的搶手貨,價格之高令人咋舌。
是的,我們就是在這種潛移默化中慢慢適應環境的變化,從一門心思專注于藝術和學術轉變為對日益蠻橫的市場的唯命是從。關于市場對藝術和學術的有益或是有害不是我要談論的話題,其中的因素太復雜了,關系到每個具體的不同的對象。我只是提問,在現今,市場上那些炙手可熱的藝術家的及其作品,是不是可以作為藝術史研究的材料?因為,從國際上成熟的藝術市場看,市場是跟著藝術史走的,換句話說,凡能夠進入并在藝術史占據地位的藝術家及作品,才值得收藏和投資。這里面所起作用的環節很多,美術館、博物館、公共藝術機構和贊助制度,專家和收藏家等等,形成了一個相互關聯和相互制約的循環系統,金錢在其中只是一種標簽,代表了某個藝術家或某件作品的價值和認知度。
我想指出,盡管藝術史是市場的最終標準和尺度,但對于當代藝術家和作品而言,以往的藝術史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因為一切都在發生和發展中,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淀和淘洗,我們無法找到現成的依據。例如,張曉剛、方力均等人,他們何以變為眾人矚目的名家呢?結論應該是,他們創造了自己在中國當代藝術中的獨特性,缺少他們,便給書寫中國當代藝術史帶來嚴重缺失。按此說法,可以推斷出一個規律,即使那些發生在我們眼前的藝術現象,亦可以從新穎、獨特和獨創這種角度來判斷某些藝術家及作品的價值。
有一次,我與國外一家著名博物館的負責收藏的研究人員交談,向其請教這方面的知識,她的一個觀點讓我記憶頗深,她說,最簡便的辦法是,收藏那些在以往藝術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新圖式、新材料、新手法之類作品,里面一定會出現未來的卓越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一定會進入藝術史。她還說,這一點上,畫商有時候比專家更善于挖掘新人新作,其敏感度超過了藝術史家和批評家。聯系到開頭我說的故事,能夠證明,市場永遠不會決定藝術史的走向,但我們對藝術史的檢索,有很多結論可以從市場的表現得到驗證:藝術史不是孤立的,尤其在當代,它是在市場中獲得養料的,兩者的關系并無尖銳沖突。因此,我還得補充一句,真正的購買是對藝術史的購買,真正的收藏是對藝術史的收藏。
藝術害苦了多少人?
我沒有統計過,全國有多少掙扎在生存線上的藝術家,以及更多的這樣的后備軍? 就我身邊的情況而言,許多立志要當藝術家并以此謀生的人正在經歷“成名”前的苦難:生活拮據,心情黯淡,經常怨天尤人而又盼望出現奇跡。這是不難體諒的。藝術家在我們的時代不是稀缺資源,藝術與市場的關系又那么密不可分,大多數想當藝術家的人是奔著有名有利去的,目的性非常明確,一切與此無關的東西都變得無足輕重。
平心而論,任何人都應該爭取過上好日子,藝術家并不例外。不過,古今中外的無數事例告訴我們,催動藝術家不斷奮斗的力量不是過好日子的愿望,因為這樣的愿望實在是太初級了一些,有許多其它辦法可以達到。我不想在這兒做啟蒙教育,講述那些優秀藝術家的故事,我只打算直截了當說,為了過好日子來當藝術家的人趁早收手,下這樣的賭注風險很大,到頭來好日子沒過上,藝術也沒起色,多讓人窩心啊!
俗話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一大幫后起者把那些名利雙收的藝術家當做刻意模仿的對象,或多或少帶有消極色彩。一位不斷與我談論自身處境的學藝中年,掛在嘴邊老是那幾個人的名字:方力均、岳敏君、張曉剛……他大概常常做這樣的比較,一旦時來運轉,自己也會與那幾個人一樣,名氣很響腰包很鼓。但是,我沒法與他說,他的才智平平,藝術上毫無建樹,名氣響起來腰包鼓起來的可能性似乎太小了。
我想以這個例子說明一個道理,其實藝術是不害人的,害人的是藝術之外的東西。這么多人眼巴巴地等著靠藝術過好日子,藝術是佛么,會普渡眾生么?我覺得如果剔除過于實際想法,藝術給人生的益處反倒會突現出來。馬克思說,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人人都是藝術家。博伊斯則把藝術的概念加以擴大,宣稱現在人人都可以是藝術家。這樣看來,藝術與人生不是一個實際的利益關系,而是通過藝術來挖掘和拓展人生的豐富性。當然啦,我不敢發揮得太玄乎了,空洞的大道理誰都會說。我還是善意地提議,那些吊在藝術這棵樹上急切地盼望著過好日子的人,如果可能的話還是早點下來,干點別的也許更好。
有話直說
前不久,老友來訪,不免談論一些藝術方面的事,不料老友有心將我們的隨意談話錄了音,并整理成文,我看了一遍,雖然了無新意,多是些老生常談,但有的問題還是具有針對性。正好《當代美術家》雜志約稿,于是我征求了老友的意見,把我們的談話加以修改和節選,發表出來,以供讀者參考和批評——以下便是我們的談話:
友:我注意到,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批評家大多變成了活動,變成了被人詬病的“趕場子”的人,他們出現在各種熱鬧的利益場所,做一些與身份無關的事情,做為批評家,你覺得這現象正常么?
李:正常和不正常是以某個標準來衡量,這個標準是什么?說實話,我無法確立它。批評家變成活動家,到處趕場子,除此之外,他們還能做什么呢?假如他們呆在書齋里辛辛苦苦寫文章,讀者在哪里?假如他們的苦思冥想只是自娛自樂,誰肯堅持?這里,我不得不用黑格爾那個歷史主義的宿命命題來做擋箭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這么說吧,批評家的好時光已經不復存在,批評家的發言權雖在但無人理會……
友:你指的好時光怎么理解?
李:若干年前——具體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批評家有一度是很風光很出彩的。他們幾乎掌握著所謂的話語權,是某種價值指向的制定者,是是非得失的評判者,是貌似書寫歷史的一群思想和觀念的精英。這顯然與當時的社會狀況相一致。因為改革開放初期,社會的價值指向尚不明確,很多事物處于尚未展開的雛形之中,需要有人批判、叫喊、推動等等,給了批評家用武之地,這是曇花一現的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