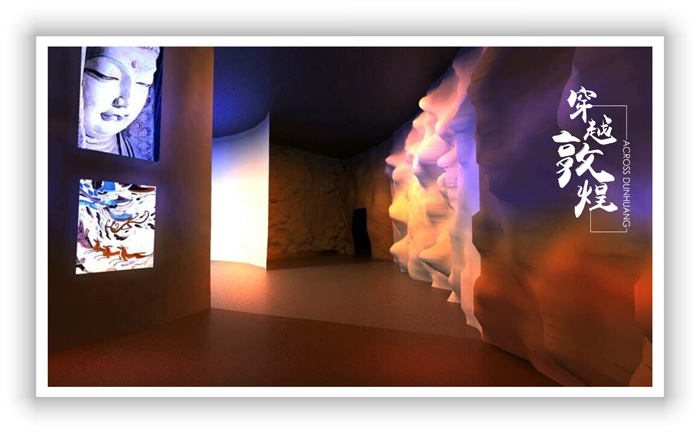劉慶和:水墨的“文藝復興”

校車 90×75cm 2014年 紙本、水墨
中鋒用筆
與傳統水墨固有的認知不同的是,劉慶和將傳統水墨中的墨色作為灰顏色在畫面中處理,而不是將其作為畫面的基礎色。而通過墨色本身冷暖間的變化,就能表現出空間的質感、遠近、厚度和溫度,拓展了傳統墨色的表現力。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墨分五色”,劉慶和創造了一種在西畫思維之下的對于墨色的認識和實踐。重要的是,在用西畫思維來運用傳統墨色的同時,并未滑向沒骨-水彩-西畫的邏輯線索,所以劉慶和在此時更加強調中鋒、畫面的留白和墨色的渲染。有時甚至會強調書卷的氣息和筆墨的偶然性,盡量用傳統樣式和文人風骨來彌補西畫的氣息。劉慶和的立場始終站在傳統水墨語境中,他的所有創新和嘗試都是基于傳統水墨的邏輯和審美,并非盲目跟從西畫的系統,相對于僅僅將水墨當作繪畫的材料,劉慶和更愿意將傳統水墨作為一種折返的語言,一種與傳統水墨本身對話的工具和媒介,劉慶和始終在和傳統水墨本身對話。
在抽象水墨實踐的藝術家中,劉慶和恰恰認為與傳統水墨有關聯的作品才是有其獨特價值的,而拋開傳統水墨進入西畫樣式的作品則變成了空洞的沒有感受力的繪畫語言。這種西方式的水墨作品還遠遠比不上西班牙藝術家安東尼•塔皮埃斯(Antoni Tàpies,1923-2012) 筆下肆意流淌的水墨線條。 與其用自己的材料來抒他人的情,還不如就用自己的材料來表達自我的情懷。因此,傳統水墨中的中鋒用筆則成為不能丟掉的一種自我的繪畫語言,這是一種發聲的武器和有力的語言。
“水”是“墨”的靈魂
對于墨色的控制,劉慶和習慣用潤澤的筆法來表現情緒的起伏和事物的質感。羊毫筆飽含水分的特質就要比狼毫的硬朗更具表現力,水分就好比是筆法的靈魂,讓畫面顯得生動而富于變化。即使在運用枯筆時,劉慶和也會用濕潤的羊毫筆來描繪枯筆的轉折。即使有枯筆的成分出現,劉慶和也會用大面積的潤澤的筆法來簇擁它,使整個畫面生動起來。此時,“水”就成為一種能夠活化色彩與機理的一種調和劑,在這個千變萬化的介質的作用之下,墨色才有了情緒,而帶有水分的墨色在交融和留白的過程中,成就了畫面的感染力,也將個人化的細微情緒通過水墨傳達給觀者。
新水墨
新水墨的意義可能正是在于跳出傳統水墨固有的技法和語言的程式化,生發出一種新的,從個人出發的水墨語言表達方式。就像文藝復興中對于人性的釋放和贊頌,新水墨也是一種對于社會固有意識形態的逆反,通過自我的藝術語言、審美體系和價值觀,來表現當下的題材。而在此過程中,傳統水墨是一個重要的前提,一切的“逆反”都是基于傳統水墨而言的。這就是劉慶和并不認同用傳統水墨來描繪西畫的原因。而以劉慶和為代表的一代所開啟的“都市水墨”題材,則正是用一種全新的視角來觀看我們當下的生活,從宏大敘事集體無意識的使命感中將自己擇出來,重新睜開眼睛審視自己所處的時代,以及時代中的個體,這讓人想起古代文人畫中的文士情懷,相對于官方畫院的八股,顯現出靈光四溢,而這些靈光都是來自于個體對于生命的體悟。后來被多次提及的“新文人畫”可能正是延續了這種個體意識之下的文人傳統和風骨,這是一種在血脈中流淌的東方哲學精神。而無論是“新水墨”還是“新文人畫”的產生,都是上個世紀的85之后所產生的,在新時代思潮的風起云涌之下,“新水墨”就是翻卷其中的浪花,而一切的動力都來自于尋找個體價值的回歸,這可能才是新水墨的意義所在。而剛結束的“白話”個展,正是劉慶和重新回溯在宏大敘事中曾經“丟失”的個人歷史。
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