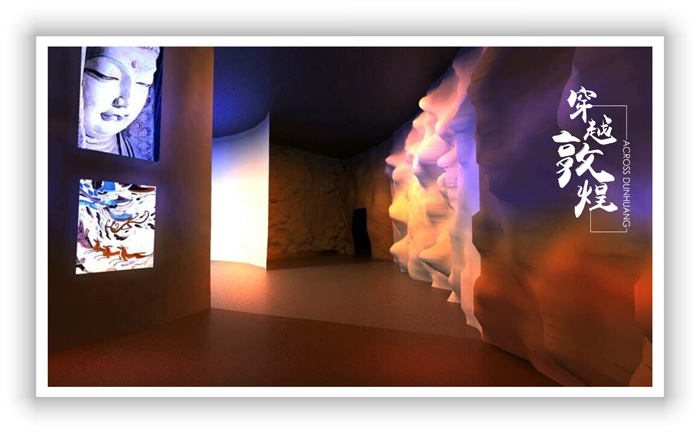保護書法的生態環境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伴隨著經濟和文化的大發展,中國書法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展賽不斷、市場繁榮、群眾性書法熱持續升溫,書法教育、書法創作、書法理論等都得到長足的發展。然而,在“史無前例”的書法運動熱潮中,濁浪排空,泥沙俱下,書法的生態環境同樣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玩弄權術,輕視學術;拉幫結派,占山為王;掠奪書法資源,攪亂書法市場;暗箱操作,近親繁殖;騙財騙色,自欺欺人……非藝術因素愈演愈烈,將書法由修身養性的藝術裂變為追名逐利的工具,道德缺損,腐敗蔓延,亂象叢生,書法生態危機四伏。
一、書法生態環境被破壞的表現形式
1、權貴壟斷,盆盈缽滿 中國是個“官本位”很重的國家。千百年來,“官”意味著社會政治地位,意味著等級特權,“官本位”思想深深地滲透到國人的每一個細胞之中。老百姓對“官”往往另眼看待,對“書法官”更是刮目相看,以其身份地位的高低來取代他們作品的藝術價值。不管是收藏界還是畫廊,不管是包工頭還是企業老總,都紛紛沖著“書法官”的大作奔去。而“書法官”又利用手中的職權奪取書法資源,操控展覽賽事、霸占書法市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乎,一盆盆白花花的銀子便收入囊中。除了官員對書法市場的霸權侵襲,少數名家也利用他們的名聲地位撈取暴利,作品動輒幾萬幾十萬一幅,形成“寡頭壟斷”,而成千上萬的普通書法家作品即便水準很高價格適中,還是少人問津,這樣書法就成了權貴們的饕餮盛宴,平民書家就只能覓食些殘羹剩飯。
2、山頭林立,你爭我奪 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國,這個“王”那個“派”就不斷在歷朝歷代瘋狂地上演。而今時過境遷,書法界某些人竟然紛紛拉幫結派,占山為王:以某“書法官”為中心,集結一大批有話語權的人組成后盾,形成“霸王”勢力;以某名師為中心,一大批徒子徒孫吶喊上陣,形成“門派”勢力;以某區域為勢力范圍,驅逐“外來和尚”,大搞“圈地運動”;以某學術為名,自立這個“主義”那個“觀念”,這種“藝術”那種“書法”,甚至自封為“總舵主”……拜碼頭、拉圈子,瓜分勢力范圍,形成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團。一個利益集團就是一座山頭,各個山頭之間明爭暗斗,互不相讓。本該清凈、和諧而圣潔的書法界儼如江湖,一時充滿烏煙瘴氣。
3、展賽泛濫,陷阱重重 當下書法界,全國展、紀念展、雙年展、單項展、提名展、精英展……中華杯、國際杯、蓓蕾杯、夕陽杯,寫經賽、楹聯賽、正書賽、榜書賽……席卷全國,泛濫成災。我們并不否認展覽賽事對群眾書法熱的推動作用,也不否認重大展覽賽事在全國或地區對書法活動的引領與指導作用。但書法展賽中魚龍混雜,我們更應正視不少展賽假借書法的名義踐踏書法的事實:有的展覽在收取作者的評審費后,還將大量的“遺漏”佳作占為已有,私分出售;有的比賽在層層盤剝作者的費用后,給你一個空頭封號或一本“光鮮亮麗”的證書,讓你竹籃打水一場空;即使是所謂的正格的書法展,也會弄得你疲憊不堪、心力交瘁,甚至某些頗具“權威性”的書法展、書法賽也會演變成交易展、交易賽……展覽不斷地傷害展覽,比賽不停地挫傷比賽,讓人不知不覺地掉入其所設的重重陷阱之中。
4、魚目混珠,市場混亂 當代“市場價值論”喧囂塵上,在利欲熏心下,各路人馬朝市場紛至沓來。毋庸置疑,市場帶動了書法藝術的繁榮,但市場的魔力,又誘使人們爭先恐后地奔向其中,宛如百米賽跑的最后沖刺:官員書家首當其沖,將書法市場權力化,任意切割;教授書家全力以赴,將書法變成聚寶盆,漫天要價;演藝書家“客串”市場,高價出售;草民書家東奔西走,擺攤賤賣。學院書法、山寨書法、江湖書法也來搶占市場,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按頭銜制定潤格、按級別確定出場費。有的百般包裝做足了“字外功夫”,以劣品忽悠百姓;有的“外倚奸商,內托官僚”,用俗品欺詐買家;拍賣會上贗品泛濫,藏家叫苦不迭……書法市場上以次充好,以假當真,一片騷亂,鬧得雞犬不寧。
5、培訓火爆,重技輕文 近年來書法培訓如火如荼,少兒班、成人班、老年班,國展班、精英班、導師班,集訓班、速成班、沖刺班……應有盡有,火爆異常。不可否認,書法培訓能有效地提高學員的書寫技巧和審美能力,對書法普及也有很大的推動作用。然而,當下的書法培訓大多是沖著“名”和“利”而來。一方面,學員急于出成績,辦班者更急了,一旦學員有作品參了展,得了獎,便有廣告可做,借以擴大招生。于是,以“速成”誤導學員,成了辦班者的一大絕招。什么“一周寫好字”、“99天速成法”,多么吸人眼球。以“國展”、“國賽”誘惑學員,什么“秘訣狠招”、“展賽風向”,極富魅力,令學員蜂擁而至,辦班者的腰包便鼓了起來。可是,這里沒有學養的含金量,也缺乏虔誠與敬畏的氛圍,只有各種寫字技巧的習練。諸如此類頻頻的培訓,不僅把浮躁之風帶進了書法教育的起始階段,也悄悄地把書法推向了功利的深淵和文化的沙漠之中。
6、跟風狂熱,復制抄襲 為了迎合展覽,當代書壇跟風猛烈——章草風剛剛消停,又刮起了書譜風。王鐸風還沒有停歇,又揚起了二王風。流行簡牘時瘋狂地寫著簡牘、流行殘經時拼命地寫著殘徑……有的集古字寫唐詩,有的琢磨評委風格寫楹聯,有的臨仿獲獎作品寫宋詞,有的直接抄襲他人之作送展覽。某個書家以某種字體或樣式一炮打響后,仿效者便如鯉魚過江般一涌而上,加上款式“大制作”,如法炮制。像這樣的一味跟風、臨仿固然對扎實書法的基本功,繼承書法優良傳統有一定的作用,但不能融會貫通,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加以創新,形成自己的風格,如是一大群面目相似、基因相同的“克隆羊”便紛紛列陣于展廳之中,使書法在惰性的環境中漸漸喪失生機與活力并由此黯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