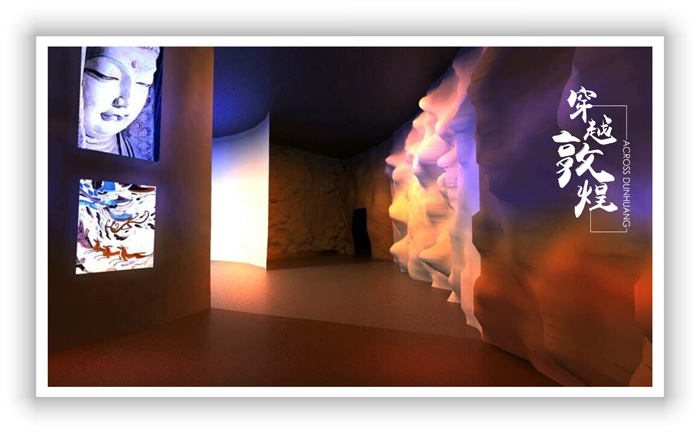何桂彥:秀美、空靈是雅公作品中的重要特點
編者按:2014年12月7日,“畫如是說——雅公心意山水作品展”在中華世紀壇二層世紀大廳開幕。展覽由策展人、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夏可君策劃,中共樂山市委宣傳部指導,樂山市商業銀行、樂山市文聯主辦,雅昌藝術網、樂山日報社、峨眉當代藝術研究會承辦。共展出藝術家雅公“心意山水”、“禪意峨眉”、“禪荷”、“云水青衣”四個系列近八十幅作品。同時,由夏可君主持的研討會于下午2時召開,雅昌藝術網執行總編謝慕、中國美術館策劃研究部主任張晴、 四川美院當代藝術研究所所長何桂彥、中國美術館青年學者、批評家王萌、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美術系教授王端廷、美術批評家及策展人、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學術部副教授王春辰、中國美術家協會《美術》雜志執行主編尚輝 、樂山市文聯副主席兼秘書長任承家和樂山市美術家協會秘書長、嘉州畫院副秘書長趙典強作為嘉賓出席研討會,就雅公的心意山水解讀并發言。
雅公先生理解的山水有三個層面:自然界的山水、內心的山水和紙面上的山水。“心意山水”不是自然山水的表現,也不是紙面山水的痕跡,而是內心的流露。研討會上,青年批評家王萌首先發言,他認為雅公的山水以心為導向與創作形態相結合,解讀了藝術家的創作與學院正統繪畫的差異;張晴從藝術家的心態與創作環境角度論述獲取“心”與“意”的文化淵源和養料,表明古今畫家親近自然,游離山水之間,無不與此有關;王春辰、何桂彥則從雅公繪畫的筆法和構圖、黃賓虹水墨畫與雅公山水畫的氣韻和作畫方式予以分析,提出問題;而王端廷回到雅公畫面本身,對他未來筆墨和境界將會達到的更加純熟純粹的境地表示期待。
何桂彥:我是四川人,四川清山綠水,樂山我也去,秀美、空靈是雅公的作品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北派山水跟南方整體來說,尤其是宋以后,南方山水整個審美趣味、用筆以及觀看方式都有一個大的變化,西南這邊我們的山水畫傳統確實不像北方那么延續。八十年代以后重新挖掘陳子莊,這個傳統相對比較弱。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我們雅公的山水畫沒有自己的特點。
聯系到這次主題“心意山水”,當說到“心意”或是“禪意”的時候,就繪畫來講,我聯系到北宋早期的繪畫是“可行、可居、可觀、可游”,換句話說山水好不好的第一條件是必須有“像”,人要進入畫面,跟自然、環境的觀看,那種觀看不是一個單點透視的三維,而是一個全身心的感受。我們在說北宋山水不僅非常具象寫實,也是人跟自然在畫面過程中“空間”結構的視覺化。當我們談“心意山水”時它的前提是什么?最初的時候一定有一個“物象”,由這種“物象”到了后來的山水畫要談“心意”,第二個階段開始慢慢拋棄“物象”轉向“筆法”和“語言”。
文人畫趣味,尹吉男先生做過一個研究,他說文人畫的提法、趣味的生成核心要跟北宋以來的徽宗、宣和畫院的趣味拉開距離,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是當時文人畫家在宋的身份相對邊緣,從宋四家到元四家一筆草草,從具象到筆法再到后來的吳昌碩,都有一個核心的方法在改變:就是過去的“物象”開始由“筆法”和“結構”取代。
第三,從物有具象到筆法再到“心意”,“心”到底由什么來承載?不能把它太玄乎了。因為你是視覺藝術,沒有任何辦法離開最后的結果。所以在雅公的作品中有幾個地方會發現,從他山水畫局部中可以非常明確地感覺到黃賓虹繪畫中的某一局部或是某種視覺結構的轉化。
另外是他的簡約和極少,我們所說的“少即是多”或者是可君說的通過“白”為畫面提供意境,我認為不管是畫面的結構還是留白一定具有“法度”,不能太隨意。過去的繪畫語言和山水傳統雖然“養人”,但是傳統有它的規范,入筆一動手,你來自于什么地方?你的譜系、筆的說法一定有依據。“法度”、“結構”得有更明確的特點,不然這個“心”太玄乎。
在以書法入手,以簡約、空靈、意象最后形成的“心意山水”,這種“心意山水”背后就是“禪”的出現。它的語境是什么?
我覺得“感受”是要從書法入畫,追求筆墨轉變,簡約、意象,我個人建議是一定得有“法度”、“傳承”、“說法”,這樣會走得更遠,而且會更加主動。
《周易》“象外之象、以外之意”,歷代畫論都在講,09年高名潞老師提出的“意派”也提到這點。傳統的國畫和西畫、油畫、裝置最大的區別就是一出手就有說法。
夏可君:筆筆有來歷。
何桂彥:這個說法要有上下文規范,而不是我們發明一個概念和詞匯放在那兒就成立。在這方面再有一個結合、提高。可能后續的創作思路,還有他所呈現的可能性會更高,這是我想說的內容。
夏可君:謝謝何桂彥。桂彥是做抽象的,有視覺的意識,現象學的理論,“心”在宋代是丘壑,元人筆墨,明代的性情,清代是金石帶進來,如果到了現代二十世紀齊白石、黃賓虹之后帶什么進來,山水往后怎么走,在哪兒?這個問題很值得討論,學術界沒有人討論這個問題。雅公他自己講“心意山水”是他的命名,他自己取名“心意山水”,確實是從天高云淡或是“心意”里出來的,到底是什么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你剛才說的幾個很好。如果宋代山水丘壑有一個形象,筆墨構造一個形象,黃賓虹把筆墨保留住了;心,董其昌是比較心意的,禪意,他也是受禪宗影響,南北宗,到了當代的“心”是什么樣的“心”?肯定不是傳統那顆“心”。我問過雅公,他有一個作品叫《獨心》、《一心》。他這個“心”是一個現代個體的心,如果不是現代個體的“心”怎么可能有當代性體現在你的“心”、物象法度上?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你的“心”跟傳統的“心”有什么差別?當代性在什么地方?這個是值得討論的。禪宗、禪意在當代是什么意義?(責任編輯:麥穗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