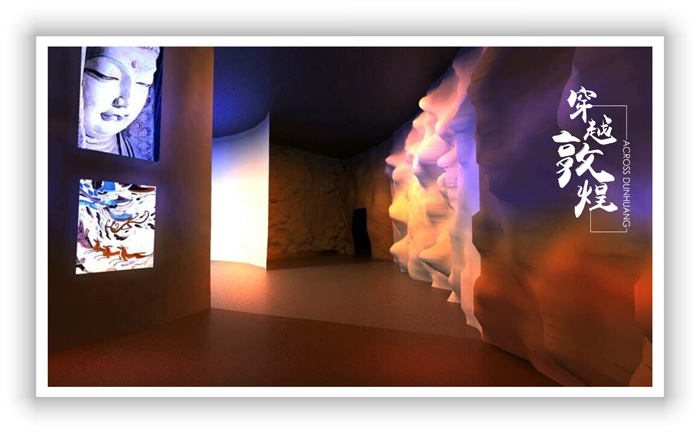假我韶光數十載 更將碩果獻堯天——訪陜西師范大學教授霍松林先生
而《訪于右任先生故里》(二首),其一云:
嵯峨山下白渠濱,毓秀鐘靈降偉人。愛國熱忱燃筆底,詩豪草圣冠群倫。
其實,詩中的“愛國熱忱燃筆底,詩豪草圣冠群倫” 二句,雖是吟誦于老之句,但若用來形容霍松林先生本人,又何嘗為過!
形象思維兼兩論 當代文心再雕龍

1951年初,霍松林赴西北大學師范學院(該學院1953年從西北大學獨立出來,改名為西安師院,后改名陜西師范大學)任教。從此,霍松林走上了一條專力于教學、科研而又崎嶇坎坷的人生道路。
到校伊始,霍松林就承擔了文藝學、現代詩歌、現代文學史三門新課。在極少參考資料的情況下,他只能邊學邊教,自己動手,擬出提綱,一節一節地編寫講義。到了1953年秋,幾經補充修改,完成了26萬字的《文藝學概論》,由學校打印,先后作為高等學校的交流教材和函授教材。因供不應求,由校方推薦給陜西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正式出版。這樣,便有了我國最早的一部新型文藝理論專著。
“本書的主要特色在于堅持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如果說邏輯與歷史統一的特色使《概論》獲得了歷史的厚重感,變得深刻,那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特色,又使《概論》變得富有生氣,顯得生動。”

文藝理論家、浙江大學中文系主任陳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藝理論研究述評》中這樣說道:“《概論》不僅開了建國以后國人自己著述系統的文藝理論教科書的風氣之先,而且發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講義與函授教材流傳,影響及于全國,大學師生、文藝工作者、中學語文教師以及文藝愛好者,不少人都從中得到教益,受到啟發,筆者即其中的一個。不少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學中文系學生,其中有些今天已成為專家,還不忘《概論》在當年如春風化雨給予他們心靈的滋養。”(《人文雜志》1988年第2、3期)
文藝理論家張炯先生指出:該書“對文藝的審美特征,包括藝術的形象性、典型性、審美功能、內容與形式、題材與風格的關系等等都有相當詳盡的論述,正是有助于讀者全面地去把握文藝的審美規律。”對于指導廣大作家和文學愛好者進行創作,也起了“不容忽視的積極作用”。(《文學評論》,1989年第5期)
《概論》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究不可沒,它更具一種界碑的價值和意義。
1982年,經過對《文藝學概論》的增刪修訂,霍松林完成了37萬字的《文藝學簡論》,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兩論”是霍松林先生研究文藝理論的力作,也是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研究領域的力作。作為教材,它把一代代學者引入文藝理論的殿堂;作為理論專著,霍松林先生構建了體大思精的理論體系,對許多重大理論問題都有獨特的見解,決不隨波逐流,決不蹈襲他人,自成一家之說。(孫明君《霍松林先生治學門徑管窺》)
“兩論”的顯著特點之一是體大思精,包容宏富,具有嚴密的系統性和突出的獨創性。舉凡文藝的特質、作品的構成、文學的種類和創作方法等等,無不納入著者的視野,覃思精慮,別類分門,條分縷析,新見迭出,充滿著一種理論開拓的勇氣和智慧。史的眼光和明確的現實針對性是兩部書的第二大特點。通讀“兩論”,我們感觸最明顯的是作者那種不拘不囿、繼往開來的史心識力,是那種立足現實,為解決當前文藝難題而努力思考的情懷。諸如文學的民族性問題、建立中國現代格律詩的問題、創作方法與世界觀的關系以及賦、比、興與形象思維的關系等問題,無不論析精到,立論允當,兼及古今,而又有著明確的現實指向。(尚永亮《浩氣由來塞天地 高標那許混風塵——霍松林先生學術傳略》)
由此,“兩論”被學術界譽為“當代《文心雕龍》”,實在是確當至評!
1956年,《新建設》5月號上發表了霍松林《試論形象思維》的長篇論文.,是國內以專題形式論述形象思維的第一篇理論文章,產生了廣泛反響,啟動了有關形象思維的第一場學術論爭高潮。
陳志明教授評價說:“(20世紀)5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部廣有影響的文藝理論教科書,60年代后期因為早年發表過形象思維理論而險遭滅頂之災,僅僅這樣兩點,就足以使建國以來的文藝理論批評無法抹去霍松林的名字。”(《霍松林先生的文藝理論研究述評》)
誰能料到,在“文革”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下,先是《紅旗》雜志1966年第5期刊登了鄭季翹(時任吉林省委書記、宣傳部長,分管文藝工作)的《在文藝領域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對形象思維論的批判》一文,其中點名批判了以群、蔣孔陽、霍松林及李澤厚等人。在此文中,鄭季翹多次點霍松林的名,引述他的有關論述無限上綱,說什么“所謂形象思維論不是別的,正是一個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正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的一個認識論基礎”。緊接著,《光明日報》又將此文全文刊登。

但凡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兩報一刊”在當時具有何等至高無上的地位!被“兩報一刊”點名批判在當時又意味著什么!很快,霍松林就被其時尚存的西北局定性為“西北地區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向陜西師范大學派下工作組,專門組織批判。當“文革”中各級機關癱瘓后,霍松林又被校內造反派組織輪番進行批斗、抄家、關牛棚、監督勞改、掛牌游街。(霍有明《“滋蘭歷劫又飄香”——家父霍松林先生印象》,《名作欣賞》 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