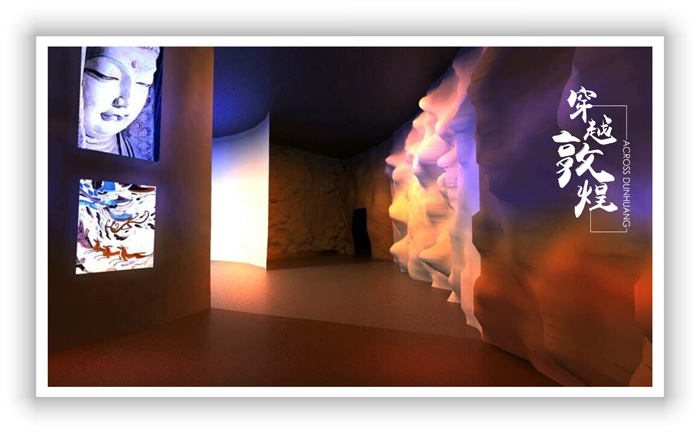假我韶光數十載 更將碩果獻堯天——訪陜西師范大學教授霍松林先生
形象思維,是文藝理論史上一個基本的命題。又稱藝術思維。最早使用這一概念的是別林斯基。關于形象思維的內容,文藝理論史上并不統一,關于它在文藝創作中的作用也有爭論。我國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出現過關于形象思維的討論,但都是學術性的。鄭季翹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維,把它當作“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來批判,說它是“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潮的一個認識論基礎”,是“某些人進行反黨、反馬克思主義活動的理論武器”。學術問題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問題,明顯體現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氣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維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邏輯”,也是不符合主張形象思維的觀點的實際的。
人們知道,深譜詩歌創作規律的毛澤東,一向是主張用形象說話,不主張簡單說理的。就在鄭季翹文章發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給陳毅的信中,毛澤東就發表了這樣的意見:
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聽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據此可以知為詩之不易。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蠟。以上隨便談來,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古典絕不能要。
正因為毛澤東對形象思維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張“要用形象思維方法”,所以,鄭季翹的文章剛一發表,他就注意到了,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兩次對其進行評說。看來,毛澤東是明顯不同意鄭季翹的觀點的。他說“不大好懂,沒看完”,其實就是一種態度。
1978年1月,《詩刊》發表《毛澤東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加在霍松林頭上的種種罪名才有了推倒的機會。此時,他已有整整十年不能動筆了!
1979年,《文藝研究》第一期發表了鄭季翹《必須用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解釋文藝創作》一文。文章不僅繼續為發表于1966年《紅旗》上的那篇文章辯護,而且采用無限上崗上線的一貫做法,用政治帽子壓制學術研究。這種狀況如果持續下去,文藝界剛剛開始的思想解放運動,必將夭折。
當時,隨著對“黑八論”的平反,全國文藝界對形象思維的大討論也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任《陜西師大學報》主編,后任陜西師大黨委書記的謝振中先生走進霍松林家,力邀他為學報第4期撰寫一篇關于形象思維的長文,在形象思維的大討論中撥亂反正。當時,距師大學報第4期的發稿時間已僅剩下八天了!
那時,霍松林才剛剛獲得徹底平反,各項知識分子政策尚有待落實,家中仍可說是“蝸居”。沒有科研條件,他白天就全天伏在平房后院內的一張小飯桌上奮筆疾書,晚上則“焚膏油以繼晷”,每天的寫作時間都在十六小時以上。八天之后,一篇題為《重談形象思維——與鄭季翹同志商榷》的兩萬多字的長文面世了!學報編輯部立即拿去排版!這篇文章,不但旁征博引,對形象思維理論重新進行了全面、深入的闡發,而且鞭辟入里,對“文革”以來反形象思維的種種謬論及其危害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反響極大。
全國著名美學家、復旦大學教授蔣孔陽先生給霍松林來信說,讀君作,“大有暑天飲冰之感!”記得事后有人稱贊道:“霍先生就是腦子靈,筆頭子快。”但是,他的家人都清楚,“十年浩劫”中,當他被造反派輪番批斗、抄家、游街時,當他被放逐到涇陽農場牧羊時,霍松林早已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為這篇文章打腹稿了。這篇文章,霍松林已在胸中整整寫了十年!
“形象思維”在當代中國經歷了大起大落的命運。當它處于學術爭鳴的范圍內時,是學術民主、思想解放的良好時期;當它溢出學術范疇,演變成敵我性質的政治斗爭時,也正是學術尊嚴、真理良知遭受踐踏的非常時期。今天反思這個問題的意義在于前事不忘,后世之師。(蔣鵬舉《霍松林先生與上世紀我國形象思維理論的論爭》)
如今,關于“形象思維”的論爭已經塵埃落定,是非曲直早已有了公論。回憶當年因為學術爭論而橫遭迫害,霍松林先生對往事仍然了了在目,只是在平靜的語氣中,還隱隱透露出當年那場論爭的激烈。
巨鐘重鑄振唐音 一代騷壇唱大風
霍松林先生幼承家學,秉性愛詩,從十五六歲就沉潛于詩詞創作,大學時代從師于著名詩人汪辟疆、胡小石、陳匪石、盧冀野諸先生,并受知于于右任先生,詩名遠播,飲譽騷壇。在以后的歲月中,霍松林始終沒有間斷詩詞創作。1988年,他把陸續搜集到的舊作和抄家后的新作編為《唐音閣吟稿》,約600首,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隨后,臺灣百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用繁體字直行排印出版,改名為《唐音閣詩詞集》。
《吟稿》共收詩6卷,詞1卷,其中詩約530首,詞44首;在各體詩中,五、七古近百首,五律50余首,七律100余首,五、七絕280首。
從表現內容看,舉凡國計、民生、親情、友情、個人際遇與感受,乃至山川勝跡,無不納入作者視野,而其中最為突出的,乃是對民族歷史行程和個人際遇的反映。從藝術特點看,《吟稿》諸作或激情奔涌,雄放不羈,或深沉渾厚,境高意遠,或含蓄蘊藉,一往情深,具有多樣化的藝術風格。(尚永亮《浩氣由來塞天地 高標那許混風塵——霍松林先生學術傳略》)
正如程千帆教授所說:“松林之為詩,兼備古今之體,才雄而格峻,緒密而思清”,卓有眾體兼擅的大家氣象。
劉君惠先生在為《唐音閣吟稿》所作的序中說:“松林游嵩山少林寺有‘巨鐘重鑄振唐音’之句,尤昭昭然自明本志矣。松林之標舉唐音,在《吟稿》中累累申其旨趣:‘須抒虎虎英雄氣,要鼓泱泱大國風’,此松林所以頌唐音也;‘論文今始窺三昧,管晏經綸稷契心’,此松林所以尊李杜也;‘翡翠蘭苕雖可愛,還須碧海掣鯨人’,此松林之審美觀,亦其詩境也;‘立志仍須追稷契,傳薪豈必效黃陳’,此松林對詩歌發展史之卓識也。舉此數端,可以概見唐音閣詩學之指歸矣。”
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諸如屈原、杜甫等不少偉大詩人,用自己充滿激情的詩筆記錄民族的災難、社會的變遷,代萬民發心聲,為時代做詩傳。霍松林先生是研究中國古典詩詞的專家,他清楚了解這個道理并深有體會。因而他的創作也發揚了這一優秀傳統,這從他詩作的題目中就能看得出來。如《蘆溝橋戰歌》、《哀平津,哭佟趙二將軍》、《聞平型關大捷》、《八百壯士頌》、《驚聞南京淪陷,日寇屠城》、《喜聞臺兒莊大捷》、《驚聞花園口決堤》、《欣聞日寇投降》、《解放次日自南溫泉至重慶市》、《“文革”書感》、《“文革”中潛登大雁塔》等等。時代造就了詩人,詩人也以他的詩作為時代的進步、為國家的富強、為民族的振興而吶喊、而謳歌。而且,這些作品,一如歷代杰出詩人的優秀詩篇一樣,總是充盈著真實、飽滿、充沛的感情。(劉鋒燾《霍松林先生的學術研究》,《文學評論》2007年第5期)